第一次从短视频里看到“丝光汤”这个梗时,我顿了一下,继而哑然失笑。因为当时我正在厨房里切丝瓜,旁边的碗里是刚打好的鸡汤液。
丝瓜蛋汤,是这个漫长的夏天里,我周末最常做的一道菜。它做法简单,耗时短,且口感清淡,在炎热的天气里也让人有食欲。堪称懒人做饭天花板。不过,要是我妈知道我经常做这道菜,估计她会戏谑地笑问我:“你以前不是不吃丝瓜吗?”
是的,在去上大学前的十几年里,我都对丝瓜敬而远之。

作者供图
在我的老家,丝瓜是常见蔬菜之一。人们不仅在菜园里种,还会在院墙下、树下、老房子的屋檐下,扔几粒种子,藤蔓就会往上爬,结出一串串长长细细的丝瓜。夏末秋初,丝瓜大量成熟,“高产似母猪”。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丝瓜炒蛋,丝瓜蛋汤,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丝瓜霸占餐桌的那段时间,往往是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虽然条件还算可以,父母也从不在吃喝上节省,但农事讲究时令,他们要争分夺秒地干活,没法留太多时间做太精细的饭菜。一碗丝瓜蛋汤,省时又营养,是不二之选。
但我一直觉得丝瓜瓤子软烂的感觉,很像某种软体动物,触感和口感都让我不适。加上家里削丝瓜皮的活一般由我承担,生丝瓜皮那股浓厚的青气,也让我感到刺鼻难闻。总之,不论是生的还是熟的,我都对丝瓜很不待见。
对于我的挑食,父母并不太在意,也没有刻意纠正。我妈总是体谅我,说她小时候也挑食,对不喜欢的菜,是真的没办法下咽。
有次吃晚饭,桌上照例有一道丝瓜蛋汤。端上来的时候,碗压到了一双筷子。我当时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不在焉地直接去抽碗下的筷子,导致汤泼出来一些。我爸干了一天重活,疲惫又饥饿,忍不住说了一句:“怎么搞的,就不知道先把碗端开,再拿筷子吗?”他一向性格温和,对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这是很少见的“重话”了。我觉得委屈,快要哭出来。我妈在一旁看了,心疼我,回怼我爸:“不就是一碗汤,洒了就洒了,少吃一口也没什么。”我更添内疚,感觉自己破坏了家里一贯的温馨氛围。
这件因我玻璃心引发的小事,更让对丝瓜增添了心理阴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别说吃了,光听到“丝瓜”二字我都感到膈应。
后来我去南方上大学,食堂的饭菜与老家口味差别很大,主打清淡,油盐很少,酱醋什么的更是少见。有一道花生米,有两种做法,一道水煮的,一道油炸的。我发现,吃水煮的一般是广东同学,吃油炸的多是外地同学。不知道是因为气候湿热,还是我骨子里喜欢清淡饮食的基因觉醒了,我很快适应了食堂的饭菜。
我的一位大学室友,按现在的说法,是“江浙沪独生女”。我们晚上开卧谈会,她说起她小时候挑食,家里的米生虫了,她妈妈就拉灯,说这样就看不见虫子了;她不吃西红柿,她妈妈就连做一个月的西红柿。如此几次,终于改掉了她的挑食。我很震惊,第一次反思自己的这个毛病。
可能是因为地域相隔遥远,我在大学很少见到丝瓜,几乎快忘了这道菜。后来辗转回到长三角,又常常见到。在单位食堂和外面餐馆里吃过几次后,我惊奇地发现,现在的丝瓜已经没有我小时候见到的那种长而软的瓤子了,这大大地降低了我接受它的门槛。有次逛菜市场,我鼓起勇气买了两根回家,削皮的时候,我又发现,也没有了记忆里那股浓重的气味。想来,是品种经过改良了吧。我甚至吃出了别的蔬菜没有的清甜味。
我与丝瓜终于达成了和解。以此为契机,我开始尝试小时候不吃的鸡鸭肉、茄子、姜蒜、辣椒……虽然有些仍然谈不上喜欢,但总算愿意慢慢敞开心扉,去接纳它们了。
我想,一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大概也是对待自我和世界态度的缩影。抛开固执和偏见,以更开放的心态,去尝试没有尝试过的,总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论结果和结论是什么,哪怕仍然不接受,体验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收获。
回到这次的“丝瓜汤”梗,其本质是代际沟通的错位。父母希望将自己过来人的阅历和经验传授给子女,让他们“少走几十年弯路”;子女则更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希望父母少一点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说教和经验传授。
很难说谁对谁错,或者说本就没有谁对谁错。不过以我的经历看,每个人、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丝瓜汤”要喝。父母们不必急于一时,现在不“听劝”的孩子,总会在他们人生的某一刻,感受到“丝瓜汤”的美味和价值,自觉对其甘之如饴。人生的路,如“小马过河”,终究要自己去走,经验要靠自己去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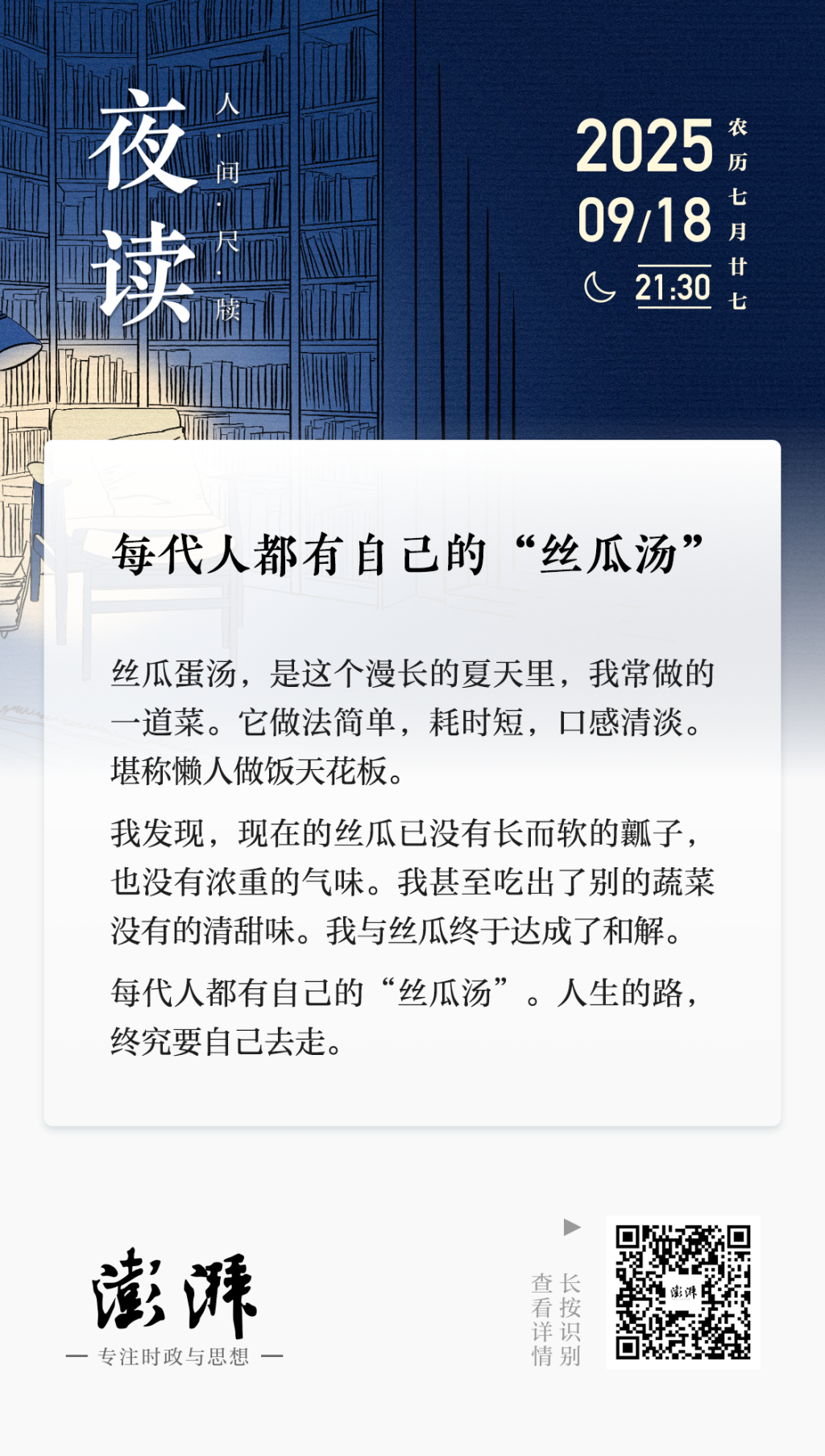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