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疯狂动物城》里,动物们拥有自己的文明、职业与社会规则,建构出一个充满寓言色彩的世界。然而,现实中动物的命运又是如何被真实的历史进程所塑造?当“牛马”从埃及乡村消失,它们究竟去了哪里?人与动物的关系,又如何映照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生存逻辑?
耶鲁大学查斯家族历史学讲席教授阿兰·米哈伊尔,正是这样一位“动物史的侦探”。他通过《消失的牛马:埃及大转折时代的动物》一书,带领读者走进一个远比动画更复杂、也更具张力的历史现场——18至19世纪的埃及。在那里,牛马不仅是劳动力,更是政治、经济与生态变迁的核心参与者。它们的“消失”,不仅是一场物种地位的退场,更隐喻着现代性进程中劳动者、自然与权力的深刻重组。
近期,《澎湃私家历史》专访米哈伊尔教授,从动画的想象走入历史的真实,探讨动物如何成为理解近代世界转型的一把关键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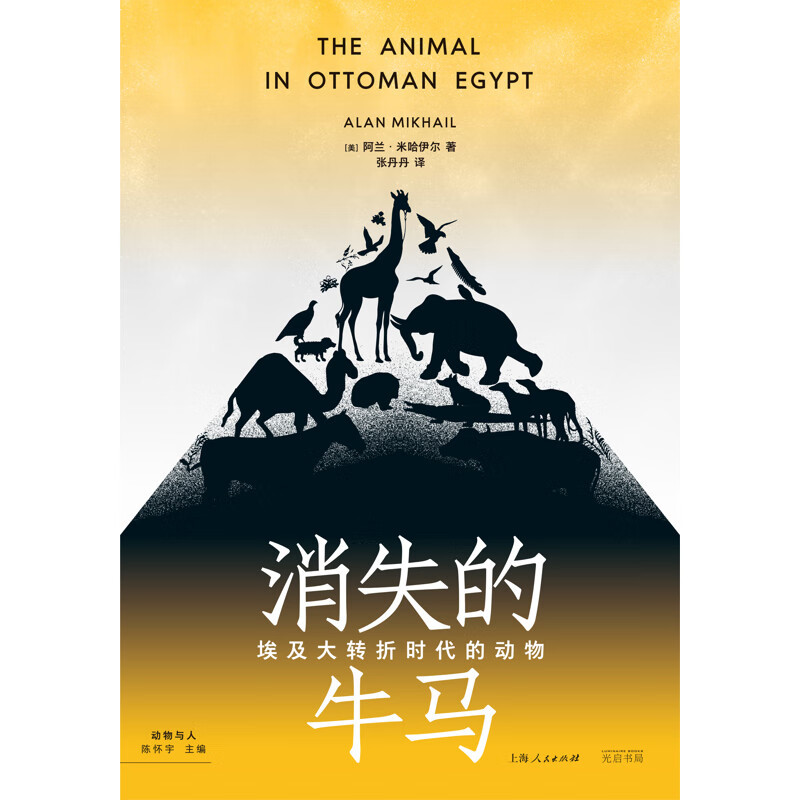
《消失的牛马:埃及大转折时代的动物》,[美]阿兰·米哈伊尔著,张丹丹译,光启书局,2025年9月出版,456页,138.00元
米哈伊尔教授,您的著作《奥斯曼埃及的动物》(中译本《消失的牛马:埃及大转折时代的动物》)最近在中国出版了,熟悉您作品的读者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埃及总是让这里的人们着迷。上海博物馆的埃及展甚至引发了一股埃及热。许多参观者对与动物有关的展品特别好奇,如猫木乃伊、猫首人身青铜像等。借此,我想问几个中国读者可能感兴趣问题。首先,您为什么选择埃及作为探究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案例?是因为埃及有很早的驯养动物的记录,还是因为埃及曾是全球动物贸易的中转站,所以引起了您最初的关注?
米哈伊尔:你在问题中提到的“中国与埃及之间的联系”让我非常感兴趣,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这一联系实际上也与你的提问密切相关。埃及和中国同为世界上拥有最长久文献记录的文明之一,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文献记录”的起点。我之所以选择将埃及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因为它的历史经验既具有独特性,又具备普适性。埃及的动物驯化史极为悠久,且与其他地区一样,孕育出特定种类的动物,同时拥有独特的地理格局。更重要的是,埃及的社会关系自古以来就围绕尼罗河而构建——从洪水的季节循环,到农业耕作与粮食生产的历法节奏——这一切都构成了埃及的特殊性,使其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我所讲述的人与动物关系的历史又具有普遍意义。我所关注的更宏大的转变,是从一个人与动物关系极为密切、共存共生的世界,转向一个这种关系仍然存在但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现代世界。人与动物的关系,对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它与家庭结构或经济形态一样,是社会生活的底层逻辑之一。这种关系贯穿古今,但又不断演变。虽然我讲述的是埃及的故事,但推动这种变化的力量——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以及气候变迁——却是全球性的,因此,这个故事也能为研究其他地区提供启发。当然,来自中国、美国或其他地区的历史学者,需要自行比较与判断:我在埃及观察到的这些转变,是否也与他们所研究的地区相契合。
中文版添加了“消失的牛马”这个主标题,不知道这个标题是否符合您最初的想法?中文里的“牛马”一词常被用作隐喻,指那些被像畜力一样驱使和剥削的劳动者。在中国大陆的职场语境中,它通常指工作量极大、缺乏自主性、被剥夺尊严的员工。
米哈伊尔:是的,这是一个很棒的修辞手法,非常贴合我在本书中想要表达的主题——动物在社会与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是如何被重新定义的。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正是探讨为何人力劳动日益取代畜力,并于19世纪初成为埃及经济体系的中心。我想揭示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简单来说,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动物的劳动角色,但现实比这种表述要复杂得多。更为关键的是,动物的命运——被剥削、被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被转移到了人类身上。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劳工,逐渐承担起了原本属于动物的社会角色:他们被支配、被异化,沦为生产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19世纪埃及的动物被压迫史,与人类劳工被剥削的历史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脉络。 因此,我认为这个中文译名还是比较贴切的。
请谈谈您为何从动物的角度切入埃及的近代社会转型,这么做的缘起是什么?
米哈伊尔:这就要提到我之前写的那本书——《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一部环境史》。书中主要讨论灌溉、粮食生产、木材输入埃及的过程,以及农业领域的劳动力问题。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各种关于乡村的资料:法庭记录、奥斯曼政府下发的乡村法令、农民针对各种问题提交的请愿书、年谱类史料,基本上能找到的资料都读了。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动物几乎无处不在。它们出现在劳动记录、乡村场景和遗产清单中,甚至出现在对理想化统治者的象征性描写里——人们会将统治者的品性与动物的特征进行比较。动物在各种资料中反复出现,而且往往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我注意到这一点,就再也无法忽视它了。我逐渐意识到,动物的重要性足以支撑起一本独立的研究著作,值得单独探讨它们在社会与历史中的角色。
在《消失的牛马》导言部分,您提到“大约在1750年至1850年间,几乎所有早期现代时期的农业社会都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剧烈转型,包括经济的商业化和现代化、城市化以及被纳入全球商品和贸易网络”,而“埃及的经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这段表述促使我们思考奥斯曼埃及研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想进一步了解,您这本书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埃及之外的其他早期现代社会(比如中国)的转型,有什么样的参考作用?
米哈伊尔:这呼应了我们之前的讨论。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世界历史叙事(虽然不一定所有人都同意):1750—1850年间,全球范围内商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是主要推动力,虽然在不同地区呈现出非常具体且差异化的形式,但仍存在一些共性。我之所以将埃及置于这样的历史框架中,特别是将埃及的人与动物关系纳入其中,是因为我认为这可以为研究其他地区提供一种参考模式,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当然,每个地方的历史故事无疑各不相同,但也会与我在书中讲述的埃及故事存在相似之处。我认为,有趣的研究问题在于,埃及模式在哪些情况下适用于其他地区、在哪些情况下失效。正如我在书中所做的,我希望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埃及的具体历史故事,但同时,这个故事也能为思考其他地区提供全球视野和借鉴意义。
您在书中指出,前现代时期人兽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和谐、互利的,而到了19世纪现代国家则强制将人兽分离。这种“断裂式”叙事是否会过于简化实际情况?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在前现代社会(正如本书第三章所示)动物也作为礼物被交换、被圈养和驯化。在强调动物能动性与人兽关系的研究中,您如何避免“浪漫化”前现代社会的风险?换言之,如何既凸显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又避免营造一种“前现代和谐—现代断裂”的二元叙事?
米哈伊尔:在导言里我提到,早期现代时期并非什么理想化的、非暴力、和谐社会,无论是人类之间,还是人类与动物之间,都不是平静无争的状态。实际上,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秩序与暴力,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但我确实认为,18—19世纪之交的过渡时期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变化。在这个时期,由于书中所追踪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动物开始更多地被视为商品,而不再被看作社会中具有活力的劳动力,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深度融入埃及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由于动物不再被视为社会的紧密组成部分,人们对它们施加了新的社会关系,其中之一便是暴力。然而,在书中我也讨论了另一种现象:关怀和反虐待的理念。在书的后半部分,我讲述19世纪出现了动物福利的观念,人们开始饲养宠物、照料动物,同时动物在肉类生产中的使用也在增加。动物被赶出经济领域的同时,这些变化也在发生。因此这一过程并非单纯从“和平”走向“暴力”,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这正是我在全书中追踪的核心线索——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变化。
您的研究也揭示了奥斯曼埃及农村社会中动物既作为劳动力与财富被严格管理,又在某些语境下展现能动性甚至与人类形成共生关系。这让我想起,在《制造宠物》一书中,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了人类与动物关系中“支配与亲密”并存的矛盾性。您如何看待这种“支配与亲密”的双重性?是否可以说,您的研究为段义孚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早期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案例?
米哈伊尔:是的,正如段义孚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却共存的现象——支配和亲昵可以同时存在,而且它们是同一组复杂关系的两个面向。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几乎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密切存在的——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与动物紧密相连,无论是通过食物消费、动物饲养,还是其他种种方式。因此,这种关系是一个既定背景。书中讲述的,就是这种关系在19世纪如何转变,并且保留其中的复杂性。为什么对某些类型的动物施加的暴力会加剧,而对另一些动物的关怀也同时在加强?我们如何在同一历史背景下理解这两者,并将它们视作人与动物关系中的不同面向?我希望我的书能够提供一个奥斯曼帝国、近代早期穆斯林世界的案例。你使用了“悖论”这个词,我很赞同。我在书中就试图证明,这或许只是表面上的悖论,实际上这二者本就密切相关,一体两面。
以我的理解,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中一个特殊的行省——无论是在近代早期还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似乎都难以直接代表或反映帝国其他地区的情况。您是否认为埃及的案例可以外推到更广泛的奥斯曼语境,还是它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例外”?
米哈伊尔:我个人倾向于将埃及视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我在研究中想展示的是,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埃及是多么不可或缺。有人可能会说,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个地区都是独特的:保加利亚有其特殊的历史,伊拉克也有自己的历史经验,埃及亦然。你的问题反映了某种史学观点,即认为穆罕默德·阿里(Mehmed Ali)的一系列行为——入侵奥斯曼帝国,让自己的家族成为埃及的世袭统治者,并建立现代国家——是埃及脱离奥斯曼帝国的例证。事实上,几十年来的主流叙事也一直认为,19世纪初的埃及打算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但学界的看法正在变化,我参考了过去二十年里一些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埃及应更多地被视作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正如我在本书和其他作品中展示的,他的行动完全是在奥斯曼帝国框架内进行的,他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奥斯曼人,而不是埃及人(尽管埃及民族主义者可能会持不同看法)。而且,这与我们之前谈到的“埃及与中国”的问题类似。埃及在奥斯曼帝国内有其独特之处,但我讲述的故事,也适用于帝国其他地区。其他学者也关注到类似的线索——比如动物劳动的使用、牲畜数量的减少,以及定居社区与牧民社区的关系——这些在奥斯曼帝国的不同地区各有特点,未必完全适用于埃及。然而,它们都是人与动物关系的故事。埃及既有其独特性,也具有普适性。
我注意到,您将本书的研究阶段界定为1517—1882,这一界定的依据很明显是重大政治事件。但环境史的研究路径往往倾向于根据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或是生态转型来作为研究的时段划分标准,您如何看待这一对张力?
米哈伊尔:我认为这是一对有益的张力。任何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时间框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讲故事,又在什么时候结束。你说得对,我在书中沿用了奥斯曼埃及的传统政治年代分期。我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希望向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学者表明,人与动物关系的历史(这种非传统的视角)实际上对于理解这一时期的埃及至关重要。当然我也明白,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气候事件、技术变革甚至洪水的季节性或瘟疫爆发,可能更有助于理解普通人的生活;或者从叛乱事件入手,可能比单纯的政治时间轴更能捕捉社会的变动。但在这本书里,我选择沿用传统的年代分期是一种战略性安排。我希望向那些怀疑人与动物关系在政治史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奥斯曼和埃及史学者说明:如果你们关心这一时期、关心这个地方,就必须关注我在书中讲述的这些故事。
我们都知道,奥斯曼帝国与中东二者间虽有重合之处,却并非完全等同。您如何看待“中东环境史”与“奥斯曼帝国环境史”研究之间的异同?如何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米哈伊尔:中东包括那些从未成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地区,也涵盖奥斯曼统治之外的时间段。因此,中东环境史比奥斯曼环境史更宽泛。它不仅涉及20世纪,也包括15、16、17世纪以前的时期,因为这里面涉及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历史进程。比如,我会将阿拉伯半岛的石油故事视为中东环境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奥斯曼环境史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故事与我在《消失的牛马》中所讲述的内容完全不同。因此,我在书中使用这两个概念,是为了区分我研究的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显而易见,摩洛哥从未属于奥斯曼帝国,伊朗也未曾被纳入奥斯曼版图。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那就是中东环境史,这是两个非常基础但必须做出明确区别的概念。
您曾提出,以往的动物研究大多关注其文化象征意义,而您则更为注重动物们的社会经济角色。这让我联想到了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教授的著作《骆驼与轮子》。在这一点上,您认为动物史如何与社会经济史进行更紧密的对话?
米哈伊尔:我认为你的问题非常准确地指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动物的劳动价值,把动物视作技术、财富、能源和交通工具。过去,动物往往被当作象征、艺术题材或文化符号,却未被视为社会与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的研究则试图打破这种偏见。整个乡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围绕动物的存在构建起来的。我常常会把动物放进一个更大的想象空间中,比如去比较两种城市:一种是在汽车发明之前形成的城市,另一种是在汽车出现之后建成的城市。两者的城市形态完全不同,因为汽车需要宽阔的街道、停车空间。如果一座城市在汽车出现后建成,整座城市的布局都会围绕汽车展开。同样地,近代早期的城市景观(虽然不能说所有地方都如此)是围绕动物而建的。街道的狭窄、城镇之间的距离,都是以动物能量所能负担的范围为尺度来规划的。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关注动物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文化象征性或政治性的动物史就不重要。
我在书中也讨论了许多关于动物的寓言和象征,比如狗的故事,以及关于大象、狮子的艺术表现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所描绘的那一方复杂的人与动物世界。我并不认为我们应当人为将这些维度拆分开来。问题在于,传统的奥斯曼史学往往忽视动物在社会中的位置。无论是在税收、供给还是战争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假设这些都是纯粹属于“人类领域”的事务,而非人类因素(non-human actors)则被排除在外。这与环境史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要认真看待非人类世界的能动性。你还提到了理查德·布莱特教授。他的研究确实是我从社会经济维度思考人与动物关系时的重要参考。他不仅关注动物的象征意义,更将它们视为社会结构与经济系统中的参与者,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在史料选用上,您在第一章利用乡村法庭记录,极大增强了叙事的地域性和细节感,但后续章节主要依赖城市编年史,使得农村环境变得模糊。您在写作中是出于史料可得性限制,还是有意识地采用了不同史料来塑造叙事?如果持续使用法庭记录,您认为对书中的核心论证会有什么不同?
米哈伊尔:我觉得你的问题非常关键,涉及到19世纪地方法庭制度变化的性质。那一时期,许多原本由地方法庭登记或处理的事务,逐渐被新设的各部委或政府机构接管。随着这一变化,地方法庭的职能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到了19世纪中后期,地方法庭更多地处理个人事务,比如婚姻、继承和财产清单等。当然,在一些案件中动物仍会出现在法庭记录里,比如涉及牲畜所有权纠纷或损害赔偿之类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我查阅的档案中,动物在司法记录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也正因如此,我在研究中主要采用那些仍能看见动物踪迹的史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史料类型的变化本身也是一种证据——它反映了动物在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下降。动物不再像早期那样在农村劳作、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中占据核心位置,而逐渐被人力取代。19世纪法庭记录更少触及与动物相关的议题,这正印证了我在书中提出的核心论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动物在社会与劳动体系中的重要性被系统性地削弱。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