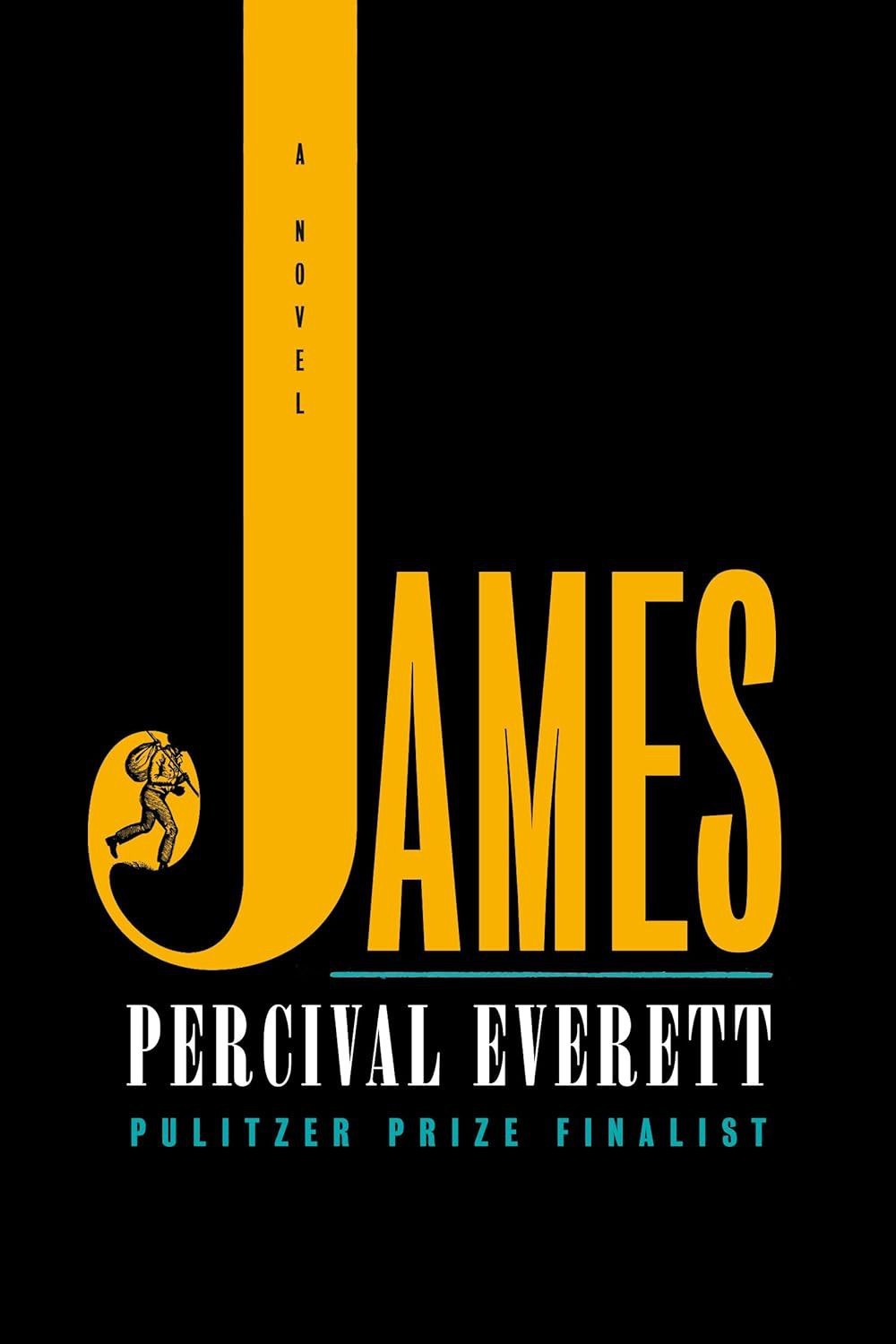
《詹姆斯》( James),珀西瓦尔·埃弗里特(Percival Everett)著,Doubleday,2024年3月出版
202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2025年普利策虚构类奖获奖作品《詹姆斯》(James),是美国黑人作家珀西瓦尔·埃弗里特(Percival Everett)的新作。小说选取马克·吐温名著《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黑奴吉姆(Jim)作为主角,以吉姆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对经典的重述。通过赋予原著中的边缘角色以叙事权,《詹姆斯》锐利地剖析了十九世纪美国奴隶制社会的深层肌理,描写了一个由语言、表演和身份伪装构成的生存环境。埃弗里特以其标志性的冷峻与智性,展现了在极端压迫下,语言既是强加的镣铐与求生的面具,亦是觉醒的武器与自由的密码;身份既是社会暴力框定的牢笼,亦是个体奋力突围、争夺定义权的战场。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曾被海明威誉为美国现代文学的源头:“所有的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马克·吐温的一部题为《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作品。……但这是我们最好的书。所有的美国文学都脱胎于此。在它之前没有过文学。此后也不曾有过能与它媲美者。”作为《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1876)的续集,该作通过白人少年哈克贝利·费恩的视角展开了一段密西西比河漂流记,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展示了一幅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的图卷,触及奴隶、种族、道德、自由等核心议题。在这部伟大经典中,黑奴吉姆(Jim)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既是哈克冒险旅程的同伴,也是其道德成长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吐温笔下的吉姆勤奋善良,具有牺牲精神,但这种典型的“老实好人”形象塑造也暴露出历史语境的局限。纵观全书,吉姆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哈克的叙事弧光,其内心世界鲜少被深入探索。此外,他也被牢牢地禁锢在一种高度刻板化的奴隶方言和忠仆的角色定位之中。这种呈现方式在吐温的时代可能具有批判意图,却不可避免地使吉姆沦为一种近乎失语的符号,其复杂的人性和主体性被遮蔽在哈克的成长故事之下。埃弗里特的《詹姆斯》,正是从这一被经典叙事边缘化的缝隙处切入,实现其颠覆性的改写。
与马克·吐温笔下那个说着刻板方言、形象相对脸谱化的吉姆截然不同,埃弗里特的吉姆拥有深邃的内心世界和惊人的语言掌控力。他在白人和黑人面前的说话方式表现为截然相反的两面,作者称这种生存策略为“情境翻译”(本文引用的原书内容均为笔者自译,以下不再另注)。在白人面前,他娴熟地操控着自己那套“正确的不正确语法”,扮演符合白人期望的愚钝且顺从的黑奴形象:“哦,老天,小姐太太,您是要俺去弄点沙子吗?”(此处使用的奴隶方言原文为“Oh, Lawd, missums ma’am, you wan fo me to gets some sand?”)。但在他的黑人同类面前,他却并不吝啬展现自己熟练掌握的标准英语,以流畅直白的语句揭示这种做法背后的生存智慧:“白人希望我们说话是特定的调调,要是不让他们失望,只会有好处”,“要是让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或许该说‘要是不让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吃苦头的只有我们”。双重语言系统是被压迫者设计出的独特沟通密码,成为他们在压迫者监视下维系联结、传递信息的隐秘生命线。这种承载了巧智的口头表演,是吉姆在长期生命威胁下的保护色,也是他戴给“敌人”观看的面具。
然而,作者赋予吉姆的反抗武器远不止于此。吉姆在逃亡途中设法寻得一支铅笔,书写的能力成为他自我赋权的转折点。当吉姆在藏身处开始记录自己的故事时,文字成为了他确证自我存在、反抗既定命运的凭借:“但我更在意的是:我在这纸上划出的痕迹,究竟能不能有意义?如果它们能有意义,那么生命就能有意义,我也能有意义。”吉姆在多段逃亡途中坚持用铅笔记录,即使处境艰难,也从未放弃通过写作梳理思绪、留存经历。事实上,读者此刻所读的《詹姆斯》,正是吉姆在逃亡途中获得的笔记本空白处写下的故事本身。“我会读书写字,绝不会让别人‘讲述’我的故事,我要自己写。”书写,成为他挣脱表演桎梏,宣告主体性的终极武器。
埃弗里特在接受《纽约客》的访谈时也提及了他对语言和意义本质的探索:“语言是骗局……因为我们希望语言有意义,它就意味一切。”吉姆的书写行为,既是解救自我的绳索,也引发了关于语言不确定性的思考。他的叙述是否完全真实可靠?他发出的“声音”是否也在某种身份意识的影响下经过了某种“翻译”?就此,埃弗里特本人常拒绝解释自己作品的含义,将意义的生成权交给读者。他称自己患有“工作失忆症(work amnesia)”,一本书出版后,他会完全忘记其内容。埃弗里特也在创作中坚持消解作者权威的原则,例如他2020年出版的小说《电话》(Telephone)就有三个版本,使读者需要面对意义的不确定性并参与建构。对语言表征能力的动摇,使得《詹姆斯》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或讽刺作品,更是一部关于叙事本身、关于如何在压迫性话语体系中争夺言说权和自我定义权的元小说。
情节上,相较于原作,埃弗里特保留了一些哈克与吉姆逃亡历程中的经典桥段,如遭遇两个骗子“国王”与“公爵”并被他们坑害等。区别在于新故事里吉姆和哈克早早便被两个骗子粗暴地分开,这也使得小说更像是吉姆自己的故事。小说中最具讽刺与荒诞张力的情节,正是吉姆与哈克被迫离散后,吉姆被卖入丹尼尔·迪凯特·埃米特(Daniel Decatur Emmett)的“弗吉尼亚吟游诗人”(Virginia Minstrels)黑脸剧团。这个剧团专职演出一种“套娃式”的剧目——因为白人不接纳黑人演员,所以剧团的黑人们要先让自己从谈吐行为上看起来像白人,再以这种伪装的白人身份出演黑人角色,从而迎合白人观赏“黑脸表演”的癖好。剧团教吉姆唱《吉米剥玉米》等带有种族刻板印象的歌曲,还用鞋油将他的手脚涂得更黑,伪装成“黑脸表演”的道具:
“别再‘先生’‘是呀’的了。”
“你咋知道的?”我怀疑地问。
“奴隶能认出奴隶。”诺曼说。
“啥?”我盯着他的脸。看不出来,但为啥有人会拿这撒谎?白人咋能看穿我?我猜可能是我说话露馅了,就像对哈克那样——这想法真吓人。
“你没露馅,”他说,“我就是知道。”他的口音太地道了,简直是双语者,精通白人学不会的那种语言。
“他们知道不?”我问。
“不知道。”
“这到底是啥?”我问,“唱歌?”
他环顾四周:“现在白人流行涂黑脸,拿我们开涮取乐。”
“他们唱我们的歌?”我问。
“有些是,还编些他们觉得我们会唱的歌。这挺怪,但不算最糟。”
“那最糟的是啥?”
“我还是先给你涂吧。”他举起锡罐说。
我坐直了,直视前方。
“准备好了?”
我点点头。
诺曼把毛巾塞到我衣领里:“别弄到衬衫上。”他把黑色涂在我额头上,“他们甚至还跳蛋糕舞。”
“可那是我们拿他们开涮的呀。”我说。
“对,但他们不懂——根本没意识到。他们从没想过,我们也觉得他们可笑。”
“双重讽刺,”我说,“挺逗的。一种讽刺能抵消另一种不?”
浅棕肤色的吉姆在剧团眼中显然还不够黑,肤色越黑,就越像一个真正的黑人。埃弗里特借吉姆所说的“双重讽刺”直白地解构了种族身份的本质,也揭示了其社会建构与充满伪装与表演性的核心。他毫不留情地展示这些演出的怪诞:“从没遇过这么荒诞、离奇又可笑的事——而我这辈子都是奴隶。我们十二个人顺着主街走,街的一边是自由区,另一边是蓄奴区。十个白人涂了黑脸,一个黑人装成白人再涂成黑的,还有我——浅棕色的黑人被涂得更黑,看起来像个装成黑人的白人。”这出身份错位的闹剧——白人扮演黑人、黑人被迫扮演“扮演黑人的白人”,将种族主义的逻辑赤裸地呈现为一场病态的、循环嵌套的表演。
通过吉姆的旅程,埃弗里特也质疑了所谓“自由”的宏大叙事。逃亡伊始,吉姆曾做过一些颇具思辨性的哲学梦境。他在梦里遇见伏尔泰和约翰·洛克,与这些代表着至高智慧和理性的思想运动功臣辩论平等、自由、奴隶制等诸种观念,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其无用与虚伪:“说实话,我怕再睡着……更怕再和伏尔泰、卢梭、洛克进行那些没用的空想对话,聊奴隶制、种族,甚至还有白化病。这世界多奇怪,这日子多荒唐:一个人的平等,得由所谓的‘平等者’来论证;这些‘平等者’得有资格发表观点,而自己却不能为自己论证;连论证的前提都得由那些不同意的‘平等者’来审核。”吉姆的终极目标并非抽象的解放,而是具体的、世俗的团圆:找到并解救被他卖掉的妻子萨迪和女儿丽兹。他的抗争之路,从语言伪装,到书写的自我确认,最终在目睹无法忍受的奴隶主强奸黑人少女的暴行后,不可避免地滑向暴力主导的复仇。他在格雷厄姆农场释放被绑的奴隶,带领他们反抗并放火焚烧玉米地,并最终向农场主开枪并与家人团聚,这似乎都在向读者传达,在极端压迫的语境下,语言和身份的伪装有其苍白的一面;个体的自由尊严,有时需要以最原始、最激烈的方式夺回。
《詹姆斯》的结尾,吉姆一家在战火纷飞中抵达爱荷华州的安全港,他平静地告诉盘问他身份的白人警察:“我叫詹姆斯。只是詹姆斯。”简单的名姓背后,是无数次的书写、表演和抗争。埃弗里特并不打算给出一个关于种族和解或美国未来的答案,他描写的仅仅是一场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个人战争,一次在语言和身份的迷失与追寻中书写真实自我的艰难旅程。夺回姓名权是小说的句点,又像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詹姆斯最终能否摆脱那个由白人凝视和种族主义逻辑搭建的囚笼?答案在此处并未言明,埃弗里特选择以其平淡而又磅礴的叙事力量告诉读者:书写自我、定义自我的意志,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自由宣言。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